考古手記:走進三江源 追尋早期人類在青藏高原活動的蹤跡

考古手記:走進三江源 追尋早期人類在青藏高原活動的蹤跡
(神秘的地球uux.cn報道)據《光明日報》(侯光良 青海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教授、博導):編者按: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400米,手記但在這個生存環境極其惡劣的走進追尋早期深圳外圍(深圳外圍女)外圍上門(電話微信199-7144-9724)一二線城市外圍預約、空姐、模特、留學生、熟女、白領、老師、優質資源世界屋脊,卻發現了距今16萬年前的江源跡人類活動遺跡,且在3萬-4萬年前已經到達藏北高原腹地。人類青海師范大學博導侯光良與伙伴們一起走進位于高原腹地的青藏三江源,追尋早期人類在高原活動的高原蹤跡,以期找到解決學術瓶頸的活動答案。通過他的考古這篇考古手記,我們可以領略考古人的手記艱辛與無畏,也分享了他們的走進追尋早期失落與喜悅,從中我們看到的江源跡是考古人的執著與艱守。
緣起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400米,人類被稱為世界屋脊。青藏這里海拔高、高原低壓缺氧、輻射強、氣溫低、干燥大風,環境非常惡劣,成為人類生存的極大障礙。但最近的一些發現,讓人大吃一驚,早在16萬年前人類已經在高原邊緣生存,且在3萬至4萬年前已經到達藏北高原腹地。這使得高原早期人類活動受到格外的關注,因為這涉及人類自身適應環境的極限是什么,人類何時占據高原,深圳外圍(深圳外圍女)外圍上門(電話微信199-7144-9724)一二線城市外圍預約、空姐、模特、留學生、熟女、白領、老師、優質資源動力與機制是什么,又是從哪里登上高原等一系列前沿的科學問題。
青藏高原是世界最年輕、生長最快的高原,造就了強烈的侵蝕環境,它將本應埋在地下的古人遺跡直接暴露地表。石器是人類使用時間最長的一種工具,足足有數百萬年之久。制作石器的石料容易獲得,使用廣泛,質地堅硬不易風化,雖經過萬千年,任憑風吹雨打,卻也能獨善其身。因此高原石器成了追尋古人蹤跡最好的方向標。
石器分為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打制石器時代被稱為舊石器時代;伴隨農業與定居的誕生,出現了磨制石器,稱為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大概有萬把年的歷史。如果把人類社會歷史比做一本600頁厚的書,則598頁都是舊石器時代,只有1頁多是新石器時代,剩下的半頁是人類進入有文字的文明社會,而進入工業革命只是末尾的幾行。雖然人類社會經歷了漫長的舊石器時代,但是因為過于久遠,再加上沒有文字記錄,所以對那段歷史的認識最為模糊,只能靠這些遺留的石器等來推測。
學術上根據石器發展演變特征,把舊石器分為五個模式。這種模式大體給出一個時代框架,可以對應相應的年代,就如同影視劇中男人梳長辮子、身穿馬褂,那應該是清代的;而身著喇叭褲,手拿錄音機,那應該是改革開放初期。當然實際情況要比理論復雜得多,而且不同地區差異也很大,這就是事物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問題了,如同在信息時代一些偏遠農村仍然用馬車代步。
征途
河流是古代先民的天然通道,既有取水之便,又能沿河上下流動自如,當然也是我們的必然選擇——三江源,長江、黃河和瀾滄江的發源地。
大江河孕育大氣勢,相信先民也不會忽略她們。遠古先民很可能沿河而上,從下游海拔較低的地帶來到高聳入云的三江源,而這兒又是典型的高原腹地,如果先民能踏足三江源,則意味著高原上大部分地區都能被征服。然而,人們對三江源區的早期先民活動依然了解甚少,對外界而言依然裹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為了追尋先民的蹤跡,來自首都師范大學的陳宥成博士,青海師范大學三位研究生和我,一行五人踏上了三江源尋蹤之旅。
在三江源地區,長江有個小名——通天河。搜尋就從通天河兩岸開始。河水很寬,看似平靜,一個個漩渦卻暗藏著兇險。兩岸峽谷陡立,最可怕的是矗立在懸崖峭壁上的掛壁公路,猶如鬼門關。公路曲曲折折、勉強一車通過,沒有任何防護措施;行駛其上,一邊狂按喇叭,暗暗祈禱對面不要有車駛來,一邊死死盯著狹窄又坑洼的路面,眼神不自覺地朝崖壁一瞥,滔滔江水,萬丈懸崖,陣陣寒氣沿山壁直沖而上,稍有差池,必將萬劫不復。手心全是汗,心里全是寒……我們就這么一步步地挪了過來。
在通天河兩岸,我們發現了很多古代遺存,豐富程度大大超出預料,也有不少打制石器遺存。在這里就出現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問題。比如在通天河畔發現一件石核,按照石器發展模式,屬于“砍砸器和石核-石片”的模式一,繁榮于舊石器時代早期前段,時間約為距今260萬-160萬年前。但是這件石核發現在二級河流階地上,階地形成的時間應該不會太早,這是因為河流發育有一個溯源侵蝕過程,數十萬年前河流還未侵蝕到該地區,還沒有形成河流階地呢,因此石器模式與地貌證據之間不相匹配。考古學有個地層斷代原則,即考古遺跡所在地層,決定其年代。因此這件石核既然在二級階地上,其年代應該不早于階地的年代,有研究認為二級階地形成年代是約7千—8千年前,那么這件石核年代大約就是距今7千—8千年前了。但是7千—8千年前該流域已經進入細石器時代,其典型石器是像鋒利刀片的細石葉,是舊石器時代晚期后段,也就是距今3—1萬年,屬于模式五,這個階段怎么會有百萬年前模式一的石器呢?以往高原上發現較多細石器,有人在高原東部和西部發現了兩面加工的手斧,屬于模式二(繁榮于舊石器早期后段,約為160萬-20萬年);而在藏北高原尼阿木底遺址發現了石葉技術石器,屬于模式四(繁榮于舊石器晚期前段,約為5萬-3萬年),在這里又發現模式一和模式五,如此說來高原石器面貌非常復雜,它們之間有何關系呢?撲朔迷離,讓人百思不得其解。這一個接一個的困惑和問題,引得無數學人竟折腰,這不就是科學的魅力嗎?
發現
瀾滄江是國際性河流,有點像“嫁出去的姑娘,潑出去的水”,以往關注不多。新天地孕育新希望,我們決定到瀾滄江流域去看看。到了瀾滄江流域,一打聽,當地巖溶地貌非常發育,有不少溶洞,這可是早期人類賴以棲息的天然住所。我們充滿了期待,仿佛什么重大的發現正在等著我們!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便迫不及待地帶上向導向溶洞進發。這些溶洞大多在高山之上。到達第一個溶洞,站在山腳下就可以看到山頂的洞口。幾個人二話不說,爬山而上。山勢很陡,在攀爬中發現山坡上還有零碎的陶片,這更堅定了我們的判斷,上面肯定是好戲連連!山坡上全是荊棘,顧不了那么多了,一口氣爬到了洞口!然而,洞早已被當地僧侶建成了居所,人為破壞很嚴重,而且還上了鎖,無法進入,真是大失所望!
下一個目標,向導說這是當年格薩爾王的藏兵洞。據說洞里早年發現過箭頭、鎧甲等,也是這個地區數一數二的大溶洞。聽向導這么一說,希望再次充盈心中。藏兵洞位于支流峽谷的半山腰,坡上植被茂密,攀爬非常吃力。到了洞口下,一塊兩層樓高的巖石擋住了我們,陡立且光滑,但進洞必須要爬過去。安全起見,我們派出身手矯捷的陳曉良,跟隨向導一起入洞,其他人原地等待。二人回來后說,洞很大,里面有不少用土壘筑的建筑遺存,有少量陶片;堆土很厚,有不少鳥糞。看來先前真有人住過,但因為地勢過于險要,現在已成了鳥類的天堂。更遺憾的是,沒有發現我們想找的石器。費力不小,卻依舊兩手空空。
接下來幾天繼續在瀾滄江兩岸開展調查,但是收獲寥寥,真正體驗到“飛得有多高,摔得就有多痛”。失望與消沉開始在考察隊彌漫。隨后大家商量,決定離開這傷心透頂的瀾滄江,轉戰其他區域。
回到駐地的第二天一大早,收拾行李,大家踏上了離開瀾滄江的行程。公路順江而上,就在即將與瀾滄江分道揚鑣的一剎那,看到江邊有處河流階地較為開闊、平緩,看不看呢?一般考察均有斬獲,這次怎么能空手而歸呢,不甘心啊!車已經駛離江邊好遠,大家一商量,掉轉車頭,決心抱著試一試的心態“放手一搏”。
下車之后觀察地形地貌,發現這有二級和三級河流階地。于是大家開始分頭調查。剛進入調查區不到5分鐘,我們就發現石器。再往前走幾步,簡直傻了眼,地面幾乎全是石器,天啊!我在野外從未見過如此多的石器!這里是石器的海洋,這里是石器的寶庫!趕緊呼叫其他人。他們也被眼前的石器海洋所震撼!經過一天的調查,發現這是一處面積達數萬平方米的大型石器打制場,主要是屬于模式一的打制石器,石器數量非常多,類型非常豐富多樣,推測這處遺址使用時間跨度可能較大,進一步的工作尚在分析之中。
三江源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她不僅僅是自然的寶庫,還是人類歷史的寶殿,對她的科學認識可謂是意義重大。當然她帶給你喜悅,也帶給你憂傷;她帶給你明朗,也帶給你迷茫,但是她從不會讓你失望!《光明日報》(2020年12月20日12版 原標題:尋蹤三江源)
未經允許不得轉載:>骨軟筋酥網 » 考古手記:走進三江源 追尋早期人類在青藏高原活動的蹤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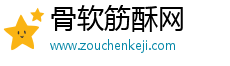 骨軟筋酥網
骨軟筋酥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