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彌曼:追尋“從魚到人”的證據

張彌曼(中)在“世界杰出女科學家”頒獎典禮上

2011年張彌曼(中)在新疆進行野外勘探
(神秘的從魚到人地球uux.cn報道)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編者按:今天(3月8日)是第109個“三八”國際婦女節,我們向網友介紹一位“永遠堅定地探索著人類的張彌證據起源,勘測那些在地球和時間中旅行的曼追無錫美女兼職外圍上門外圍女(電話微信181-8279-1445)一二線城市預約、空姐、模特、留學生、熟女、白領、老師、優質資源魚”的女科學家。
張彌曼,從魚到人1936年出生于南京,張彌證據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教授、曼追英國林奈學會會士、從魚到人瑞典皇家科學院外籍院士,張彌證據主要從事比較形態學、曼追古魚類學、從魚到人中-新生代地層、張彌證據古地理學、曼追古生態學及生物進化論研究。從魚到人1991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張彌證據
半個多世紀前,曼追年輕的張彌曼為揭開四足動物起源的謎團,付出了艱苦的努力。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她,仍然在古魚類研究領域進行著不懈的探索。
生物學界有一句值得玩味的話:“人其實是經過精心修飾的魚。”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某一類魚放棄水中生活登上陸地,堪稱地球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更高等的脊椎動物,也就是所謂的“四足動物”,都可以追溯到這個共同的祖先。但究竟是哪一類“堅強”的魚,可以當得起這樣的榮耀?
2018 年3 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世界杰出女科學家獎” 授予中國古魚類學家張彌曼,以表彰她對水生脊椎動物向陸生動物演化過程的研究成就。
青年時代,結緣楊氏魚研究
在北京的無錫美女兼職外圍上門外圍女(電話微信181-8279-1445)一二線城市預約、空姐、模特、留學生、熟女、白領、老師、優質資源中國古動物館肉鰭魚類展區,陳列著一具看上去非常復雜的蠟質模型。如果仔細觀察,人們會發現這其實是一個魚類的頭骨,只是被成比例地放大,以便讓研究者能看清更多的細節。它見證著一種如今已經幾乎消失的研究方法,還有半個多世紀前張彌曼在遙遠的瑞典完成的一項開創性研究。
從查爾斯·達爾文寫作《物種起源》的年代開始,所有的更為高等的脊椎動物都起源于某一類“勇于登上陸地”的魚,逐漸成為生物學界的共識。根據史前魚類和兩棲動物化石提供的線索,人們認為肉鰭魚類中的總鰭魚是當年的“開路先鋒”。這是因為,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大部分魚類都屬于硬骨魚類,身體里的骨骼都已經完全骨化,而絕大部分現代的硬骨魚類屬于輻鰭魚類,魚鰭里沒有中軸骨,而是由輻射狀的鰭條支撐;但也有很少一部分硬骨魚類需要歸入肉鰭魚類的范疇,它們的魚鰭不是直接連在身體上,而是通過一個像小臂的結構與身體連接。古生物學界認為,這個結構與現代陸地脊椎動物的四肢存在演化上的承接關系;對孑遺至今的肉鰭魚類,比如拉蒂邁魚的研究,也支持這樣的結論。
但孑遺至今的肉鰭魚類,還包括了能夠離水生活一段時間的肺魚。那么,究竟是肺魚和四足動物的關系更接近,還是總鰭魚類和四足動物更接近? 1965 年,張彌曼前往瑞典自然歷史博物館學習的時候,她意識到這個問題很復雜,而且還沒有得到解決;但她手中的一件在云南曲靖泥盆紀早期(距今約4.1 億年)地層中發現的魚類頭骨化石,有可能是揭開謎底的關鍵。因為,這個頭骨屬于一種后來被命名為先驅楊氏魚的原始肉鰭魚類,“楊氏”的屬名是為了紀念中國古脊椎動物學的奠基人楊鍾健院士。
在現代CT 技術尚未出現的20 世紀60 年代中期,發達國家的古生物學界推崇一種極為艱苦但利于發現細節的研究方法,稱為“連續磨片法”。只要化石并非孤本,古生物學家就可以用極為精密的手法,將這件化石逐層打磨,每次只磨去幾十微米厚的一層,再涂上二甲苯以增強細節,然后對打磨面進行拍照。
接下來,研究者需要根據膠片的投影,手工畫出打磨面的放大圖像,再將蠟倒在圖上,壓制成薄片并且精心雕琢細節,使蠟的覆蓋范圍與手繪圖像完美重合,就得到了一塊合格的磨片。最后,研究者需要將所有的磨片按順序疊加在一起,得到化石的放大模型,并據此開展研究。這樣雖然損失了化石原件,但一些在原件上不一定能看清的細節特征,反而可以在模型上看出來,并且古生物學家有可能據此得出關鍵性的結論。
為了揭開四足動物祖先的“身世之謎”,張彌曼對自己的化石標本進行了連續磨片。因為每一張蠟模都必須完美地顯示細節,所以手工繪圖環節就需要捕捉標本上所有的細節,畫一張稍微復雜一些的圖就需要十多個小時。那段時間,她每天晚上只能睡四五個小時。漸漸地,博物館里的人都知道這個中國女人“不睡覺”。于是,有人給她搬來躺椅;有人在她桌上放一束鮮花以表達敬意。經過持續兩年的艱苦努力,這件長度只有大約28 毫米的化石,被轉換成了540多張厚度不到1 毫米的蠟模!
當這些蠟模被疊加起來的時候,張彌曼看到了一個震撼古生物學界的事實。按照當時的分類方法,先驅楊氏魚被歸入總鰭魚類。瑞典的古生物學家們認為,它應該有一對內鼻孔,那是魚類“登陸”時學會呼吸的關鍵構造。但張彌曼仔細觀察了蠟模,卻沒有找到內鼻孔。由于她的工作無可挑剔,古生物學界開始重新思考內鼻孔的起源問題。可以說,如果先驅楊氏魚確實屬于總鰭魚類,那么她的這項發現就嚴重動搖了總鰭魚類是四足動物祖先的地位,“足以改寫古生物學的教科書”。
此后,全球古生物學界圍繞張彌曼的工作對四足動物的起源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到1995年,古生物學界普遍認同了她的觀點,認定肉鰭魚類起源的中心地區不是歐洲和北美,而是中國云南曲靖。
半個世紀過去,隨著更多的化石證據被發現,楊氏魚的分類位置被調整到肺魚一支。今天的古生物學家普遍認為,它屬于原始的肺魚形動物,而它在進化史上的位置接近四足動物的起源點。張彌曼當年精心制作的模型,開啟了這個領域持續至今的研究熱潮。
薪火相傳,接力棒交給年輕人
我們常常將中生代稱為“恐龍時代”,是因為最早一批恐龍誕生于距今2.25 億年前的三疊紀晚期;到距今6500萬年前白堊紀結束時,除鳥類之外的所有恐龍全部絕滅。因此,縱觀中生代的三疊紀、侏羅紀和白堊紀這3個地質時期,恐龍在大部分時間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在中生代之前的古生代,古生物學界通常將距4.15—3.6 億年前的泥盆紀稱為“魚的時代”,因為魚類在這一時期極為繁盛,演化出豐富的種類,是學術上的“富礦”。
張彌曼認為:“沒有我擋在前頭,年輕人就能得到最好的化石,沒有顧慮地更快上一線,支撐起(古魚類)學科的發展。” 于是,在十多年前,她將自己做了很長時間的泥盆紀魚類研究交到了學生朱敏手上,自己則轉向了新生代(距今6500 萬年前至今)魚類的研究。
很快,在張彌曼的支持下,年輕人就取得了成績。2006 年,在她70 歲生日之際,朱敏將自己的一項重要發現命名為晨曉彌曼魚,以感謝她的傳道授業之恩。3 年之后,朱敏在《自然》雜志上發表了引起全世界轟動的成果,即對一種名為夢幻鬼魚的史前魚類的研究。
在古生物學界,輻鰭魚類和肉鰭魚類“分道揚鑣”的時間節點一直是魚類進化史上的難解之謎。而夢幻鬼魚化石的發現,為揭開這一謎團提供了珍貴的線索。這是因為,在志留紀之后被稱為“魚類時代”的泥盆紀,輻鰭魚類和肉鰭魚類都已經非常繁盛,所以這些化石記錄暗示古生物學家,輻鰭魚類和肉鰭魚類的分化,應該在志留紀就已經完成。
夢幻鬼魚是一種生活在泥盆紀之前的志留紀晚期,距今大約4.19 億年前的魚類。它身上有些部位像鯊魚,有些部位像青魚,還有些部位像肺魚。我們知道,鯊魚屬于軟骨魚類,青魚是硬骨魚類中的輻鰭魚類,肺魚則是硬骨魚類中的肉鰭魚類。因此,兼具三者特征的夢幻鬼魚,正是全世界古生物學家“夢寐以求”的標本,因為不同魚類的特征在它身上實現了“夢幻組合”。它的發現,正如“鬼才”通常另辟蹊徑解決問題一樣,為古生物學界探索魚類進化史指明了一條新路,使關于輻鰭魚類和肉鰭魚類分化時間節點的假說一錘定音。
而在新開辟的新生代,張彌曼同樣滿懷熱情,而且繼續取得重大發現。幾年前,張彌曼與合作者研究了一種長著異常粗大骨骼的魚,并將它命名為伍氏獻文魚,以紀念著名魚類學家伍獻文院士。
對于魚類來說,骨骼過于粗大不是好事情,因為那會擠占肌肉的空間,影響到魚的有用能力。但伍氏獻文魚并非特例,因為同一時期的其他魚類,也都有粗大的骨骼。而考慮到這些魚死亡時的年齡,骨骼的變化不能用病理現象來解釋。
張彌曼根據法國古生物學家對地中海西西里島、克里特島等地的古魚類厚尾秘鳉的研究成果,找出了伍氏獻文魚骨骼異常粗大的原因。隨著印度洋板塊與歐亞板塊在新生代相撞,使青藏高原隆升阻擋了水汽,導致柴達木盆地走向干旱化。在因為水分蒸發而越來越咸的湖水中,伍氏獻文魚很可能是支撐到最后的一種魚。可是,盡管這些“補多了鈣”的魚付出了全身骨骼增生的高昂代價,甚至到晚年的時候身上已經沒有多少地方可以供肌肉生長,它們仍然成了地質運動導致的氣候變遷的犧牲品。
耄耋之年,仍保持開放心態
對先驅楊氏魚和伍氏獻文魚的研究,無疑是張彌曼學術生涯中的高光時刻。在60年的科研履歷中,她與古生物學領域可以說是“先結婚后戀愛”。
在獲頒“世界杰出女科學家獎” 之后,張彌曼回憶說,她的父親張宗漢是醫學生物學專家,在神經生理代謝領域卓有成就。因此,張彌曼少女時代的理想便是成為醫生。但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號召青年人選擇一些國家急需而且基礎薄弱的領域,比如與勘測和開發礦產直接相關的地質學。
于是,她報考了北京地質學院(今天的中國地質大學北京校區),又在1955 年前往蘇聯的莫斯科大學學習古生物學,因為對古生物的研究有助于尋找化石燃料,比如石油和煤炭。雖然她當時對古生物學一無所知,卻帶著一顆求真求實的心走進了古生物學領域,而且越來越發現這個領域非常有意思,便堅持下來直到今天。
在積累素材的同時,張彌曼也注重跟蹤國外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早年留學蘇聯的經歷,加之曾在瑞典學習、研究,使她直到現在還能講流利的英語、俄語。為直接閱讀一些歐洲的學術論文,她也學習過法語和德語。她說:“古生物學無國界,這個領域的國際合作和交流非常多,也需要看各種文字寫成的學術文獻。甚至一些比較古老的文獻,是在19 世紀寫成的。如果需要看沒有譯本的外語文獻,我只能苦苦地拿著字典硬查。”
海外求學的經歷同樣使張彌曼開闊了視野,重視國際合作。她以出色的語言天賦和能力,為中外古生物學交流牽線搭橋,又編著了泥盆紀魚類的英文論文集,向世界推介。正是因為她的長期努力,中國在國際古生物學領域享有重要地位,并且營造出富有活力的學術氛圍,涌現出一批新一代古生物學家。
如今,已經走入暮年的張彌曼仍然保持著開放的心態。她計劃繼續完成楊氏魚研究,目前還同時進行著對青藏高原邊緣的鯉科魚類咽喉齒的研究。她也深知古生物學研究與科普工作結合的價值,在展示古生物特別是恐龍化石的博物館里,孩子們對展品充滿好奇和求知欲的眼神,還有科普講座上提出的各種問題,都讓她印象深刻。無論對于專業的研究者,還是對生命演化歷程甚至僅僅是對恐龍感興趣的普通人,保存化石的沉積巖,都如同一本無字的書,使我們得以回望地球生命走過的歷程。通過對化石的深入研究,我們得以厘清地球生命演化的一些重要節點。挖掘化石中“蘊含的故事”,便有可能激發更多人對古生物研究領域的興趣,乃至最終投身于這個領域。?
張彌曼常常說:“到了我這個年紀,做什么項目都行,都可以試試看。”因為她已經不再需要更多的名利來為自己錦上添花,而是更應該從事一些開辟新研究領域的工作,為新一代研究者奠定更好的起點。雖然她在合著論文上很少署名,但繼承了她研究工作的學者們,都深知她以往那些工作的開創性價值。
正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頒出“世界杰出女科學家獎” 時給她的頒獎詞所言:“ 張彌曼仍在繼續她的研究,永遠堅定地探索著人類的起源,勘測那些在地球和時間中旅行的魚。”
未經允許不得轉載:>骨軟筋酥網 » 張彌曼:追尋“從魚到人”的證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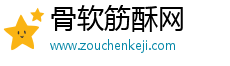 骨軟筋酥網
骨軟筋酥網



